跨越成见之山,追求真理之路
跨越成见之山,追求真理之路
——中国电影三十年“打破偏见”主题的多维透视
2025年,正值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作为重要文化载体的中国电影,不仅见证国家的沧桑巨变,也深刻影响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深刻改革,这些变革不仅在重塑社会结构,也深刻影响文化艺术的创作走向。本文纵观1995年至2025年间的中国电影,从电影文本与社会泛文本的互动角度,通过分析《变脸》、《刮痧》、《十二公民》、《我不是药神》、《第二十条》和动画电影《哪吒》系列等代表性影片,探讨中国电影如何在历史语境调适和艺术创新的双重实践中,推动公众对性别、文化、制度性偏见进行反思。中国电影在历史叙事、艺术形式与社会功能的协同演进中,既反映社会意识的觉醒,亦塑造公共理性的新范式。中国电影在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思想解放方面的独特价值,为未来电影创作提供启示。
一、“打破偏见”的主题演进与时代共振
中国电影近三十年对“打破偏见”主题的深入探讨可以追溯到1995年由吴天明导演执导的《变脸》。影片中的经典台词“菩萨也是女的”直接挑战性别固化观念,呼应改革开放以来女性意识觉醒的社会浪潮。2001年由郑晓龙导演执导的《刮痧》则聚焦跨文化偏见,讲述了一个美籍华裔家庭因刮痧治疗而引发的法律纠纷的故事,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两部作品不仅体现了这一阶段中国电影承载“文化寻根”的使命,也试图在现代化进程中探讨了民族身份的重构,并尝试通过电影艺术激发观众对于偏见、文化认同等社会议题的深度思考——《变脸》聚焦传统文化在全球化冲击下的身份困境,《刮痧》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社会阵痛。《变脸》与《刮痧》奠定了中国电影批判偏见的叙事基调,也展现了中国电影在反映社会现实、引导公众思考方面的潜力。
进入21世纪,伴随中国法治化进程加速,电影成为公民参与公共议题的重要媒介。中国电影在解构偏见主题方面呈现更加多元和深入的趋势。2015年改编自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的《十二公民》,将故事背景设定为中国某高校内的模拟法庭,通过十二位陪审员各自的视角碰撞探讨程序正义。影片构建了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以理性辩论解构阶层与经验偏见,同时展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法律公正的重要性。随后,《我不是药神》(2018)和《第二十条》(2024)等影片将目光投向了更为隐蔽的结构性。《我不是药神》通过讲述一个普通药店老板为白血病患者走私印度仿制药的故事,展现了医疗垄断下的伦理困境。一个个个体抗争的,正是这种结构性不公导致的种种偏见。《第二十条》则更进一步,借由围绕正当防卫认定的一系列争议案件,剖析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差异与权力运行机制的现实复杂性。这些影片在题材选择上更大胆,更直面社会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像《第二十条》中的台词“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深刻呈现了在既定司法框架和法律制度下进行价值判断与伦理抉择时所面临的张力。而且这两部影片在反映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需要不断调适与完善深层次议题的同时,还通过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让观众深刻感受到这些偏见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标志着中国电影的成熟和进步。
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对话,当下的中国电影在“打破偏见”的主题表达上继续升华。《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和《哪吒之魔童闹海》(2025)是这一趋势的杰出代表。它们以全球化的视觉语言重构本土神话。强烈的情感共鸣令《哪吒》系列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哪吒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也成为世界各地青年的亚文化宣言。中国电影凭借更广泛的感召力,正从本土叙事转向跨文化表达,以“新国潮”美学参与全球现代性批判。
二、艺术形式与叙事策略的革新
影像语言是意义生产的核心载体。从《变脸》中传统戏曲符号的性别隐喻,到《哪吒》系列中神话的现代化视觉重构,中国电影正在通过符号的颠覆性编码,逐一消解固有文化符号的霸权性。例如,《变脸》以“变脸”技艺为符号,通过女性继承人的设定,解构传统文化中的性别霸权——影片将戏曲脸谱从男性专属符号转化为女性赋权的象征。《哪吒》系列以“魔童”形象打破“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其视觉设计(如烟熏妆、叛逆姿态)将传统符号转化为反抗偏见的新青年主义主张。中国电影通过符号系统、叙事革新与技术赋能,构建了一套独特的解构偏见的影像话语。
在叙事模式上,早期作品(如《变脸》和《刮痧》)多采用线性叙事,以单一视角直击偏见问题。而《十二公民》采用复调叙事,通过十二位陪审员的观点交锋,模拟公共领域中的理性对话。这种“多声部”结构暗合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使观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意义共建者。《我不是药神》虽保留线性叙事框架,但通过药企、患者、执法者的多重视角,在价值预设和道德前提的差异性层面,凸显个体在偏见下的生存困境。
近年来,技术发展为影视作品中偏见议题的表达开辟了新路径与影像的更多可能性。《哪吒》系列借助3D建模与动态捕捉技术,成功将传统神话转化为具有沉浸感的视觉体验,吸引以“Z世代”为代表的年轻观众群体,通过亚文化符号及其互动式传播增强对社会议题的关注。此外,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在增强观众沉浸感与临场感的观影体验方面展现出巨大潜能。未来,新兴媒介技术介入影像叙事,不仅在视觉体验层面拓展观众的感知边界,更能够在行为模式、情感体验层面,与观众形成交互,从而推动电影叙事范式与艺术语言的革新。
三、偏见的结构性镜像与社会疗愈
社会学视角下,电影是社会结构的文化表征。以“打破偏见”为主题的早期作品,如《刮痧》中的刮痧疗法在西方现代医学体系的主导下处于边缘位置,反映全球化语境下边缘文化资本的弱势地位。影片呼吁跨文化对话,打破“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申公豹有关“成见如山”的独白,直指偏见的社会再生产机制——群体共识如何固化为结构性压迫。而《我不是药神》则体现了医疗资源的制度性垄断,揭露了韦伯所言“科层制理性”的异化——当效率逻辑凌驾于生命伦理,系统性偏见便成为结构性暴力的具象化。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开始触及偏见的再生产机制。《第二十条》中司法体系的权力规训,呼应了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法律不仅是裁决工具,更是权力规训的载体。伴随影片围绕案件调查开的叙事线索,逐步呈现了如何通过制度程序被合法化,从而引发对“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辩证关系的公共反思。
电影不仅是娱乐商品或意识形态工具,更是社会自我疗愈的仪式。中国电影在“打破偏见”这一主题下三十年来的探索证明,艺术能够以“温柔的暴力”瓦解成见之山,通过叙事及其价值观表达唤醒集体反思。正如《十二公民》促进了公众对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的讨论,提高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影片公映后第三年,即2018年4月27日,由全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陪审员法”决议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引发了全社会对高价药品问题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国家医保政策的改革。以上电影与社会的互为建构关系,足以体现出电影不仅是银幕内的幻觉与想象,更具有冲破银幕,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实践,对公众意识甚至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产生致变性作用的力量。
然而,中国电影从对具体偏见的批判(如性别、文化),逐渐转向对现代性悖论的深层叩问,本质上也是一场启蒙现代性的未竟之旅:当技术理性(如《哪吒》中的天劫咒)与人性价值冲突时,个体如何在算法歧视、数据霸权、深度伪造污名化等新偏见形态中保持主体性?这要求电影创作要超越本土语境,接入全球现代性批判的话语体系。
如本雅明所言,“电影是机械复制时代的神圣艺术”。而当其神圣性指向公平与正义时,艺术便成为了变革的预言。中国电影三十年的“打破偏见”之旅,既是社会意识的觉醒史,也是艺术形式的革新史,归根结底,是艺术、历史与社会的三重奏。从符号重构到制度批判,从本土焦虑到全球对话,电影始终扮演着“文化装置”的角色——既映射社会结构的裂痕,也缝合集体创伤。在技术异化与新冷战的当下,中国电影需以更开放的视野,将偏见议题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探索艺术表达与社会变革的共生路径,尝试偏见消解与文明共生的可能性。如《十二公民》所言:“追求真理是一件幸福的事。”而电影,正是这条真理之路上永不熄灭的引灯。
作者:北京聚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王鲁娜
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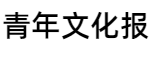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来抢沙发吧~